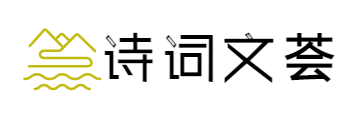
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和蔡襄的合称。这四个人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书法风格,而且成就最高,故称“宋四家”。
明清以来,有一些人认为宋四家中的“蔡”原本应该是蔡京,后人不齿其为人,所以把蔡京换为蔡襄,并认为蔡襄的艺术成就在蔡京之上。
宋代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其最主要的实践者是北宋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四人。盛时泰《苍润轩碑跋》中说:“宋世称能书者,四家独胜。然四家之中,苏蕴藉,黄流丽,米峭拔,而蔡公又独以浑厚居其上。”
一、“宋四家”与唐书的渊源
虽然宋代“尚意”是对唐代“尚法”的否定,但时代发展总是相连的,“宋四家”对唐代书法并不完全否定,因而不能将“法”和“意”对立起来看。唐代书家中,对宋代影响最大的是褚遂良和颜真卿二人。颜真卿对“宋四家”都有影响。蔡襄入宋已是暮年,笔下多是唐法。苏轼对颜真卿《东方朔画赞》极为垂青,评其“清雄深远”。留心苏轼书法,意态肥厚之处是颜真卿字态。黄庭坚说:“东坡道人少日学《兰亭》,故其书姿媚似徐继海……中岁喜学颜鲁公、杨风子书,其合处不减李北海。”王澍说:“‘宋四家’书,皆出鲁公,东坡得之为甚,姿态艳溢,得鲁公之腴。”米芾认为颜真卿行书有篆籀气,对其“三稿”极为称赞。米芾大字转折肥美,显出颜姿。黄庭坚书法对颜真卿反其道而行,中宫收紧,四面扩张,将颜书中短促的笔画加以夸张伸长,施以颤笔,形成真力弥漫的线条。至于褚遂良,其影响只针对米芾而言。米芾认为“褚遂良书举从动人,而别有一种骄色”。从褚遂良处以窥《兰亭》,这是米芾“入魏晋平淡”和“备其古雅”的捷径。
二、行书之外的书法比较
“宋四家”成就主要体现于行书,此外是楷、草两体,米芾有少量的篆、隶书作,但不值得称道。
就楷书而言,笔者认为,“宋四家”中首推蔡襄。其面目多似颜真卿,渗入很多文人气,无胜唐正大气象。颜鲁公作书,不经意的地方很多,蔡襄作书则笔笔留心,所以米芾说:“蔡襄如少年女子,体妖娆,行步缓慢,多饰繁华。”苏轼大楷法颜真卿,在字形上压扁,重视的是意态肥厚。黄庭坚《夷齐庙碑》近似褚法,稍嫌松散。米芾没有大楷传世,小楷《向太后挽词》意守欧、褚之间,颇令人称道。
就草书而言,“宋四家”中成就最高者非黄庭坚莫属。苏轼、米芾鄙薄张旭、怀素为“书工”,认为他们视书法为事业,违背书法娱己悦人的宗旨,丧失了林下之风的淡雅,而“有如市娼抹青红”。苏轼草书极为罕见,米芾草书数量也很少,线条尖薄油滑,创作行书时的自信一扫而光。蔡襄草书被称为“散草”,夹有章草遗意。他自诩道:“每落笔为飞草书,但觉烟云龙蛇,随手运转,奔腾上下,殊可骇也。静而观之,神情欣欣,可喜耳!”但苏轼认为蔡襄“大字不如小字,草不如真,真不如行也。”这三家草书和黄庭坚相比不可同日而语。黄庭坚草书作品颇丰,主要从张旭处得法。最具代表性的是《诸上座帖》,行笔如风,笔意超凡,线条如惊蛇走虺,跌宕多姿,具有强烈的抒情性。
三、苏、黄、米、蔡究竟谁排第一
苏轼在“尚意”书风中是领头人物。以“吾虽不善书,晓书莫如我”的气概引领一代新风。黄庭坚为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受苏轼教诲。留心黄庭坚手札一类,颇有苏字之风。米芾虽未入“苏门”,但听从苏轼“入魏晋平淡”的建议,取法二王,最终成就自我。因而苏轼对宋代书法有化身千百的不凡功德。他所书的《寒食诗帖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,能有这样的作品传世,可以说是平生无憾了。因而在“尚意”书风中,将苏轼排在第一应该是无可争议的。但如果要论及行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,则首推米芾。米芾在“宋四家”中年龄最小,影响却最大,连董其昌都说米芾“当在东坡之上”。
近代康有为认为黄庭坚应该排第一。他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说:“宋人之书,吾尤爱山谷,虽昂藏郁拔,而神闲意浓,入门自媚。若其笔法瘦劲婉通,则自篆来。”苏、米、蔡只有一种书体名世,而黄庭坚的行、楷和草书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,不仅称雄当世,而且溢出时代。在“苏门四学士”当中,惟有黄庭坚视苏字为“压扁蛤蟆”,由此略知黄氏的胆识。可以说,黄庭坚是“宋四家”中最具创新意识的。
蔡襄在“宋四家”中年龄最长,苏轼推崇其为“近世第一”。但在“宋四家”中,蔡襄“尚意”书风并不彰显,充其量是一个过渡人物。梁章钜《字学》中认为“宋四家,苏、黄、米皆可学,惟蔡不必学。盖蔡书尚未尽变唐人风貌,学蔡不如径学唐人”。因而潘伯鹰认为“蔡襄可当第一”的观点笔者很难认同。
四、对“意”的表现
宋代书法品评中常见“意”这个字眼,强调“意”是反叛“法”,但不是粗浅无法,而是“法本无法”,是在高度技巧承递基础上的自觉选择。元代刘有定《〈衍极〉注》中说:“今古虽殊,其理则一……庾、谢、萧、阮,守法而法存;欧、虞、褚、薛,窃法而法分;降而为黄、米诸公之放荡,持法外之意。”清代冯班《钝吟书要》中说:“宋人作书,多取新意,然意须从本领中来。”他认为苏、黄、米三人书艺超人,尤其是米芾,将外拓笔意之美发挥到了极点。明代李东阳《怀麓堂集》中说:“米书与苏、黄并驾,而各不相下。大抵苏、黄优于藏蓄,而米长于奔放。”现代陆维钊的《书法述要》中说:“书家笔势,穷极于米芾。”应该说,“宋四家”书法,气势充沛。
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,素有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四大书家的说法,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。“宋四家”中,前三家分别指苏轼(东坡)、黄庭坚(涪翁)和米芾(襄阳漫士)。从书法风格上看,苏轼丰腴跌宕,天真烂漫;黄庭坚纵横拗崛,昂藏郁拔;米芾俊迈豪放,沉着痛快。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,书风自成一格,时人推崇备至,列于四家,向无异议。唯独列于四家之末的“蔡”,究竟指谁,却历来就有争议。
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(君谟),他的书法取法晋唐,讲究古意与法度。其正楷端庄沉着,行书淳淡婉美,草书参用飞白法,谓之“散草”,自成一体,非常精妙。宋仁宗尤爱其书,曾“制元舅陇西王碑文,命书之”,又“令书温成后父碑”(《宋史·蔡襄传》)。蔡襄的书法艺术也为当时文人所重视,黄庭坚曾说:“苏子美、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。”(《山谷文集》)欧阳修说:“君漠独步当世,然谦让不肯主盟。”(《欧阳文忠公集》)苏武在《东坡题跋》中指出: “独蔡君谟天资既高,积学深至,心手相应,变态无穷,遂为本朝第一。”既然是“本朝第一”,既然其书法已可“主盟”,那么,列于四家应是当之无愧的。
然而,明清以来,又有另一种说法一认为从四家的排列次序及书风的时代特色来说,“蔡”原本是指蔡京,只是后人厌恶其为人,才以蔡襄取代了他。明书画鉴赏家张丑在《清河书画舫》中说:“宋人书例称苏、黄、米、蔡者,渭京也。后人恶其为人,乃厅去之而进君谟书耳。君谟在苏、黄前,不应列元章后,其为京无疑矣。京笔法姿媚,非君谟可比也。”明代孙镀也说;“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,今易以君谟,则前后辈倒置……”(《书画跋跋》)安世凤《墨林快事》进而替蔡京书名被掩抱不平,说;蔡卞胜于蔡京,蔡京又胜于蔡襄,“今知有禁而不知有他蔡,名之有幸不幸若此”。清杭世骏《订讹类编续编》也将“苏黄米蔡非蔡襄”,作为“人讹”的一个事例。可见,明清时“蔡京说”曾有很大影响。
平心而论, “蔡京说”的提出确有一定的道理。其一,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、痛快沉着的特点,与保待着较多“古法”的蔡襄相比,蔡京的书法似乎更富有新意,也更能体现宋代“尚意”的书法美学情趣。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,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。元陶家仪《书史会要》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;“其字严而不拘,逸而不外规矩,正书如冠剑大人,议于庙堂之上;行书如贵胄公子,意气赫奕,光彩射人;大字冠绝占今,鲜有俦匹。”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。其二,蔡襄的书法在北宋前期被推为“本朝第一”,但自北宋中期宋代书法新风貌形成后,人们对蔡襄书法渐有微词。苏东坡在《东坡题跋》中,就多次提到“近岁论君谟书者,颇有异论’”,“仆以君谟为当世第一,而论者或不然”。虽然苏轼始终坚持蔡襄为第一的看法,但至少在北宋中后期,人们对蔡襄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。其三,从排列次序看,苏、黄、米三家的排列有明显的年辈次序,蔡襄是仁宗时人,年辈最高,列于哲宗、徽宗时的米芾之后,确有些疑问。
对此,坚持“蔡襄说”者提出反驳,认为“宋四家”之说,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,但南宋遗民、元朝人王存,已明确提出过“四家”之说。他在《跋蔡襄洮河石砚铭》墨迹中称蔡襄书法“笔力疏纵,自为一体,当时位置为四家。窃尝评之,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,涪翁瘦硬通神,襄阳纵横变化,然皆须从放笔为佳。若君谟作,以视拘牵绳尺者,虽亦自纵,而以视三家,则中正不倚矣”。可见王存不仅指出当时有四家之说,而且四家明确无误是苏、黄、米、蔡。此外,在书法史上,蔡襄的书法成就以全面著称,楷、行、草书皆独树一帜,且又有屏弃帖学,振兴书风的贡献,因此,从总体上看,其成就显然是超过蔡京的。至于排列次序,近人张伯驹曾在《宋四家书》一文中指出,“按次序应是蔡、苏、米、黄,普追读为苏、黄、米、蔡,以阴阳平上去顺口,遂成习惯”。说明这一排列仅为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,与四大家的年辈高下并无关系。
看来,“蔡京说”并非无稽之谈,而“蔡襄说”也有理有据。由于蔡京身为“六贼”之一,人们从感情上实难接受他,于是人们多倾向于蔡襄说。不过,这一问题的最后定论,似乎应有待于宋代文献的确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