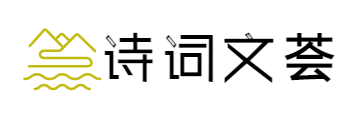
竹林七贤,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(240年—249年),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七人。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(今河南焦作修武县,可能为现今云台山一带)竹林之下,喝酒、纵歌,肆意酣畅,世谓七贤,后与地名竹林合称。
卫绍生在《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》(《中州学刊》,1999年第5期)一文中指出,“竹林”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。而陈寅恪先生在《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第三篇“清谈误国” 中认为,先有“七贤”而后有“竹林”。“七贤”所取为《论语》“作者人”(《宪问》)之数,意义与东汉末年“三君”、“八俊”等同。西晋末年,比附内典、外书的“格义”风气盛行,东晋初,乃取天竺“竹林”之名,加于“七贤”之上,成为“竹林七贤”。“竹林”既非地名,也非真有什么“竹林”。
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,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,作家不能直抒胸臆,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、象征、神话等手法,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。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。
竹林七贤,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: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刘伶、阮咸、向秀、王戎。活动区域在当时的山阳县。《晋书·嵇康传》:嵇康居山阳,“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、河内山涛,豫其流者河内向秀、沛国刘伶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,遂为竹林之游,世所谓‘竹林七贤’也。”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说他们“陈留阮籍、谯国嵇康、河内山涛,三人年皆相比,康年少亚之。预此契者:沛国刘伶、陈留阮咸、河内向秀。琅邪王戎。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,肆意酣畅,故世谓竹林七贤。”
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,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不同。嵇康、阮籍、刘伶、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,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山涛、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,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。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,清静无为,聚众在竹林喝酒,纵歌。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。
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。嵇康、阮籍、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、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。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。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,但不为司马炎所重。山涛起先“隐身自晦”,但40岁后出仕,投靠司马师,历任尚书吏部郎、侍中、司徒等,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。王戎为人鄙吝,功名心最盛,入晋后长期为侍中、吏部尚书、司徒等,历仕晋武帝、晋惠帝两朝,在八王之乱中,仍优游暇豫,不失其位,但在当时年代不失为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。
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,最后分崩离析:阮籍、刘伶、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,嵇康被杀害,阮籍佯狂避世。王戎、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,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。
他们的创作虽与建安文学有明显的不同,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,但仍然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现实,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“建安风骨”的传统的。
竹林七贤之名的由来,学界存在争议。东晋孙盛《魏氏春秋》文云:“(嵇)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(今河南省焦作),与之游者,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与陈留阮籍,河内山涛,河内向秀,籍兄子咸,琅邪王戎,沛人刘伶相与友善,游于竹林,号为七贤。”一般认为“竹林七贤”之名与“集于竹林之下”的竹林之游有关。
传统说法认为“竹林”位于嵇康在山阳的寓所附近。嵇康与其好友山涛、阮籍以及竹林七贤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间畅饮聚会,因而时人称之为“竹林七贤”。这种说法见于《晋书·嵇康传》及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竹林七贤条。
陈寅恪认为,“竹林七贤”的活动地方实际上并没有产“竹林”,竹林七贤是先有“七贤”而后有“竹林”,七贤出自《论语》中“作者七人”的事数,有标榜之义。“竹林”之辞,源于西晋末年,佛教僧徒比附内典、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,乃托天竺“竹林精舍”(Vlenuvena)之名,加于七贤之上,成“竹林七贤”。
王晓毅不认同陈寅恪的观点,从汉晋时期佛经中“竹林”这一译名的出现频率质疑了陈提出的“托天竺竹林精舍”一说,并结合史料实地考察发现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确实种植有“竹林”,之后又从时间和地点上论证了竹林七贤聚会的可能性,从而认为传统说法对于“竹林七贤”一名由来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。
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,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,肆意欢宴。后遂用“竹林宴、竹林欢、竹林游、竹林会、竹林兴、竹林狂、竹林笑傲”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,或借指莫逆的友情;以“七贤”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。
在“竹林七贤”中以山涛年事最长,且“竹林七贤”中的嵇康、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,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,因此,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。
阮籍的《咏怀》诗82首,多以比兴、寄托、象征等手法,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,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,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。
嵇康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,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,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,文章颇负盛名。
其他如阮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,刘伶的《酒德颂》,向秀的《思旧赋》等,也是可读的作品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山涛有集5卷,已佚。
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,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,导致民不聊生。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,而且时时担忧生命,因此崇尚老庄哲学,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,用清谈、饮酒、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,“竹林七贤”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。
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“道”、“无”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。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、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,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,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,自我意识、精神的觉醒和提升。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“竹林玄学”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,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评到“及正始明道,诗杂仙心;何晏之徒,率多肤浅。唯嵇志清峻,阮旨遥深,故能标焉”,“仙心”中显露“飘忽俊佚,言无端涯”的风格,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在玉雕上,海派玉雕师穆宇静借助竹林七贤在文学上的影响,进行玉雕雕刻,竹林七贤玉雕正反浅浮雕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,在竹林之下下棋,赏乐,论字画,肆意酣畅,雕工清新脱俗,2011年获得“上海玉雕神工奖”金奖,这也是古文学与今工艺的完美结合,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及思维理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