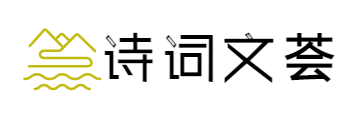
吾家石砚玄玉色,来自扶桑海中国。荡摩日月露光精,吞吐波涛含润泽。
天生奇质为世用,海王龙伯不敢匿。少时得之方外人,四座传玩皆叹息。
二十年来亲翰墨,北走洙泗西梁益。钱塘会稽屡游历,鬼神呵护同珙璧。
水怪山精皆辟易,佐我为文写胸臆。上探玄化与为敌,宣畅民彝辅皇极。
云雨布濩飞霹雳,倏忽变迁靡定迹。谬致声名惊四方,招谤速侮不煖席。
其间损益两相?,砚也于余良尽职。岂知万事不可料,昔者相亲今不得。
潼关群盗何大剧,窃瞰行人俟昏黑。金钱虽失不足叹,此砚使我深痛惜。
我非玩物有偏爱,又非昧理苦蔽惑。直伤美器不遇主,有似贤才受驱迫。
真卿奉使陷叛臣,苏武持节幽异域。忠肝义胆贯天地,岂忍包羞污凶逆。
孔子春秋至谨严,细事不肯登简策。大弓宝玉二物耳,特书盗窃惩乱贼。
我诛鼠辈恨无力,著作有心禆六籍。何时见汝生羽翼,奋飞重来侍吾侧。
不然变化为星辰,照临下土常烜赫。外物聚散如置奕,胡为念汝长戚戚。
君不见自我得之失无憾,不如萧公差达识。
庭院无人处。绮情生、镇日悲秋,悄无一语。百感填膺芒角露,恨少霓裳歌舞。
漫记忆、前身儿女。泥雪三生重印证,谱新词、遑说推敲苦。
天有缺,石能补。
生平只为多情误。触牢愁、酩酊难浇,蓬莱易沮。哀乐小年难自遣,只听琵琶低诉。
何处是、满庭芳树。但愿仙风飘引去,到珠宫、重问云霞侣。
离别久,泪如雨。
黑山东下水如潮,晓傍祠门绾玉镳。野老尚能陈往事,秋襟何啻挹奇标。
河丘勋迹晴空丽,洛社耆英故国遥。秀野囗中神注里,欲凭江雁寓芳谣。